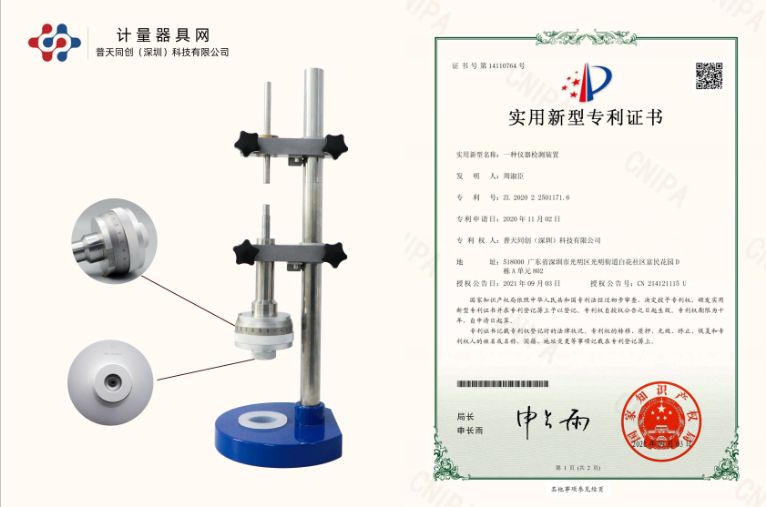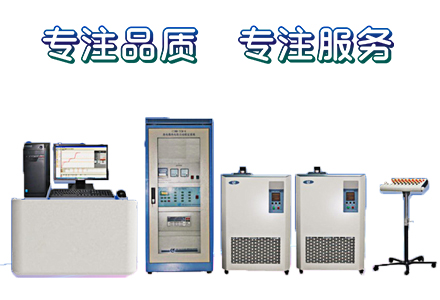那天的風雪真暴,外面像是有無數發瘋的怪獸在呼嘯廝打。雪惡狠狠地尋找襲擊的對象,風嗚咽著四處搜索,從屋頂從看不見縫隙的墻壁鼠叫似的"吱吱"而入。
大家都在喊冷,讀書的心思似乎已被凍住了。一屋的跺腳聲。
鼻頭紅紅的歐陽老師擠進教室時,等待了許久的風席卷而入,墻壁上的《中學生守則》一鼓一頓,開玩笑似的卷向空中,又一個跟頭栽了下來。往日很溫和的歐陽老師一反常態:滿臉的嚴肅莊重甚至冷酷,一如室外的天氣。
亂哄哄的教室靜了下來,我們驚異地望著歐陽老師。"請同學們穿上膠鞋,我們到操場上去。"
幾十雙眼睛在問。"因為我們要在操場上立正五分鐘。"
即使歐陽老師下了"不上這堂課,永遠別上我的課"的恐嚇之詞,還是有幾個嬌滴滴的女生和幾個很橫的男生沒有出教室。
操場在學校的東北角,北邊是空曠的菜園,再北是一口大塘。那天,操場、菜園和水塘被雪連成了一個整體。
矮了許多的籃球架被雪團打得"啪啪"作響,卷地而起的雪粒雪團嗆得人睜不開眼張不開口。臉上像有無數把細窄的刀在拉在劃,厚實的衣服像鐵塊冰塊,腳像是踩在帶冰碴的水里。
我們擠在教室的屋檐下,不肯邁向操場半步。
歐陽老師沒有說什么,面對我們站定,脫下羽絨衣,線衣脫到一半,風雪幫他完成了另一半。"在操場上去,站好。"歐陽老師臉色蒼白,一字一頓地對我們說。
誰也沒有吭聲,我們老老實實地到操場排好了三列縱隊。
瘦削的歐陽老師只穿一件白襯褂,襯褂緊裹著的他更顯單薄。
我們規規矩矩地立著。五分鐘過去了,歐陽老師吃力地說:"解散。"。
就在我還未能透徹地理解歐陽老師這一課時,僅有"中師"文憑的他,考取了北京一所師范大學的研究生。
以后的歲月里,我時時想起那一課,想起歐陽老師課后的一番話:"在教室時,我們都以為自己敵不過那場風雪,事實上,叫你們站半個小時,你們也頂得住,叫你們只穿一件襯衫,你們也頂得住。面對困難,許多人戴了放大鏡,但和困難拼搏一番,你會覺得,困難不過如此……"
我很慶幸,那天我沒縮在教室里,在那個風雪交加的時候,在那個空曠的操場上,我上了永遠的一課。